"妈,小舅参加高考,您真要用嫁妆帮他?"我看着母亲将那只红木首饰盒放进布袋,心里忐忑不安。
她只是轻轻"嗯"了一声,眼里却有我看不懂的坚定。
那是1982年的春天,我们一家住在县城边缘的筒子楼里,一间十几平米的屋子,一家三口挤在一起。
屋内陈设简单,一张木床,一个衣柜,还有父亲单位发的一台黑白电视机,是我们全家的骄傲。
晚上七点,整栋楼的人都会打开电视,收看《新闻联播》,然后是《西游记》或《霍元甲》这样的连续剧,整个楼道里回荡着同步的声音,此起彼伏。
父亲在钢铁厂当工人,每天骑着永久牌自行车上下班,车把上总挂着两个铝制饭盒。
母亲在纺织厂上班,是车间里的女工,手上常年有纺织留下的老茧,批发价买回的纱线,在煤油灯下织成毛衣,省下不少钱。
日子虽不富裕却也踏实,家里有收音机,有缝纫机,还有几张粮票和肉票贴在厨房的墙上,随时可用。
母亲的那些嫁妆——金耳环、银手镯,还有一条祖母传下的玉坠,是她最珍贵的财产,平日里锁在抽屉深处,只有逢年过节才拿出来戴一戴。
每次拿出来,她都会小心翼翼地擦拭,然后对着镜子照一照,脸上带着少有的满足。
小舅比母亲小十岁,成绩一直很好,却因为家境贫寒,初中毕业就去了生产队干活。
"脑子活泛的娃,跟着队里种地,可惜了,"村里的老支书常说,"要是赶上好时候,准能考大学。"
那段日子,小舅常常抱着从县图书馆借来的书,在煤油灯下看到深夜,眼睛熬得通红。
有时候,他会坐在村口的大石头上,看着远处县城的灯光发呆,那里有知识,有未来,有他梦寐以求的大学。
母亲每次回娘家,总会给他带些纸笔和几本书,偶尔还会塞给他一两块钱买参考资料。
有一次,我看见母亲从市场上买了两斤猪肉,却只带了半斤回家,另外的一斤半,包好了带回了娘家。
"我爸妈和弟弟,三个人总得改善一下生活,"母亲解释道,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,"咱家有肉票,他们那儿没有。"
"咱们家能不能不管闲事?"父亲坐在八仙桌旁抽烟,烟雾缭绕中,他的眉头紧锁,脸上的皱纹像刀刻的一样深。
"你弟弟又不是没手没脚,怎么老是要咱们接济?"他拍了拍桌子,震得搪瓷缸里的茶水晃动。
"再说了,你那点嫁妆,留着以后给孩子上学用不好吗?你爹娘给你的东西,你就这么不当回事?"
"老赵,你不懂,"母亲边整理布袋边说,"我弟弟是个有出息的,就是没机会。"
她停下手中的活儿,眼睛望向窗外飘落的雨丝,"现在国家恢复高考了,他要是考上大学,一辈子就不一样了。"
"可是咱家也不宽裕啊!"父亲把烟头摁灭在烟灰缸里,发出"嗤"的一声,"工厂里的奖金都发不下来,日子能好到哪去?"
"再不宽裕也比我娘家强,"母亲叹了口气,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布袋的边缘,"我要是不帮,他连考试费都交不起,更别说买复习资料了。"
"那他高中也没上完,怎么参加高考?"父亲皱眉问道。
"现在可以自学,然后参加同等学历考试,"母亲回答,声音里有少见的坚定,"我去打听过了,只要有初中毕业证就行。"
父亲看着母亲的样子,最终只是摇摇头,没再说什么。
他知道,这个看似柔弱的女人,一旦下定决心,比谁都固执。
那段时间,邻居王大妈来串门,看见母亲在收拾首饰,忍不住问:"赵家媳妇,听说你要卖嫁妆?不怕婆家人说闲话啊?"
"春草不怕牛羊踩,自有根在泥土里,"母亲微微一笑,"帮自己亲弟弟,天经地义的事,有什么好说的?"
"可你婆家也不容易啊,"王大妈压低声音,"听说钢铁厂这几个月效益不好,工人的奖金都减了。"
"再难也就这几年,"母亲把玉坠小心翼翼地放进盒子,"等我弟弟有出息了,不就好了吗?"
母亲的坚持最终战胜了父亲的反对。
那个阳光明媚的日子,我跟着母亲去了当铺,路上两旁的杨树刚抽出嫩芽,风一吹,影子在地上摇曳。
县城的街道不宽,两边是带着雨檐的老房子,行人来来往往,有推着三轮车卖冰棍的,有扛着扁担叫卖的,有穿着蓝色工装、骑着自行车的工人。
当铺在一条小巷子里,门口挂着"鑫记当铺"的木牌,已经有些掉漆了。
我看着母亲将那些心爱之物一件件拿出来,那条玉坠在阳光下泛着温润的光,是母亲过门时祖母亲手戴在她脖子上的。
当铺老板姓李,是个四十多岁的男人,戴着一副老花镜,眼睛后面是精明的目光。
他认识母亲,一边鉴定一边忍不住问:"赵家媳妇,这些可是你的命根子啊,舍得?"
"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。"母亲笑了笑,将李老板给的钱仔细折好,放进内衣口袋。
出了当铺,母亲的步子突然轻快起来,脸上的表情也舒展了许多。
回家路上,我问母亲后不后悔,她摸着我的头说:"人这辈子,有些东西比金银珠宝值钱多了。"
我似懂非懂,却记住了她眼中那份坚定,像是冬日里的一把火,能融化所有的寒冷和犹豫。
隔壁李婶知道这事后,摇着头对院子里的人说:"现在的年轻人,太不知道轻重了,自己家都顾不过来,还惦记着娘家人。"
"可不是嘛,"老刘接过话茬,"娘家兄弟有出息没出息的,跟她有什么关系?自己过好日子才是正经事。"
这些议论传到母亲耳朵里,她只是淡淡地说:"自家的事情,自家知道。"
那年夏天,我第一次见到了认真备考的小舅。
他住在县城里我家附近租的一间小屋子里,屋子不大,只够放一张床和一张桌子,却被他收拾得干干净净。
桌上摞着高高的参考书和习题集,窗台上放着几盆绿植,是他从村里带来的,说是看着心情好。
小舅瘦高个子,皮肤黝黑,眼睛却格外明亮,说话时总是带着笑,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小许多。
"姐夫,我一定不会辜负你们的,"他坐在我家的饭桌前,吃着母亲特意做的红烧肉,腼腆地说,"等我考上大学,有工作了,一定会报答你们的。"
父亲这时脸上的表情才缓和了些,递给小舅一根烟:"好好学习,别想那么多,考得上就是对你姐最大的报答。"
小舅那段时间每天学习十几个小时,晚上常常到凌晨两三点。
母亲担心他的身体,经常做些好吃的送过去,有时候是一碗面条,有时候是几个馒头夹菜。
有一次,我跟母亲去送饭,看见小舅桌上放着一个小铁盒,里面装着一块手表,是当年生产队发的奖品。
"这是我最值钱的东西了,"小舅不好意思地笑笑,"如果如果我考不上,至少还能卖了,把姐的嫁妆钱还回来一部分。"
母亲听了,眼圈一下子红了,转身出去摘院子里的青菜,掩饰自己的情绪。
那年夏天,小舅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省城的大学,全村人都来道贺。
那天,我家的小院子里挤满了人,村里的老支书还带来了一面"学习标兵"的红旗,说是全村给小舅的荣誉。
小舅站在人群中,脸涨得通红,一遍遍地说着"谢谢",目光总是不自觉地落在母亲身上。
我至今记得他临走时,握着母亲的手,红着眼眶说:"姐,这份恩情,我这辈子都忘不了。"
母亲只是笑,眼里却闪着泪光:"好好学习,别的不用想。"
小舅走后,父亲对母亲的态度也柔和了许多。
有一天晚上,我听见父亲小声对母亲说:"你看人比我准,弟弟真的考上了大学,你这个决定没错。"
母亲轻轻应了一声,没有多说什么,但从那以后,她脸上的笑容多了起来。
光阴似箭,转眼十几年过去。
1997年,国企改革大潮席卷全国,父亲所在的钢铁厂宣告破产,发了最后一个月的工资,就让工人们回家等通知了。
母亲的纺织厂也开始大规模裁员,车间里的老人优先被辞退,母亲拿着一纸解聘书回来,脸色苍白。
那段日子,家里气氛沉闷得像要下雨的天空,父亲整天坐在院子里抽烟,母亲则在市场上摆了个小摊,卖些自己做的小吃补贴家用。
我刚考上大学,面临着高昂的学费和生活费,全家陷入困境。
"要不我先不上了,找个工作帮补家用?"我对愁眉不展的父母说,心里却痛苦不已。
为了这个大学梦,我熬了多少个通宵,做了多少套试卷,如今却要被现实击碎。
"不行!"母亲斩钉截铁地说,声音里有让人不敢反驳的力量,"咱家就是砸锅卖铁,也得让你上大学!"
父亲在一旁叹气:"可是咱家现在这样,拿什么供孩子上学?"
"我多摆几个小时摊,每天多赚点,"母亲的声音轻了些,但依然坚定,"再不行,还有我那些金手镯,当年就剩下两个,现在应该能值些钱。"
听到这里,我的心一阵刺痛。
当年她变卖嫁妆帮小舅,如今又要变卖仅剩的首饰供我上学,这个瘦小的女人,肩膀上扛起了多少重担啊。
正当我们一筹莫展之际,一个意外的访客出现了。
那天下午,我正在院子里晾被子,远远地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走来。
小舅站在门口,手里提着一个公文包,风尘仆仆。
多年不见,他瘦了许多,眼睛却更加明亮有神,身上的西装虽然不是什么名牌,却很整洁,给人一种干净利落的感觉。
"姐,姐夫,我来了。"他大步迈进屋,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个信封,"这是孩子上大学的钱,全额的,够四年用的。"
母亲愣住了,父亲也放下了手中的报纸,屋子里安静得能听见墙上挂钟的滴答声。
"这这怎么好意思?"父亲惊讶地看着那个鼓鼓囊囊的信封,"你自己也不容易"
小舅当年毕业后曾回家探望过几次,我们都知道他工作不太顺利,在省城几经辗转,始终没有找到满意的工作。
"我不过是还个人情罢了,"小舅笑着说,把信封放在桌上,"姐当年若不是变卖嫁妆,哪有我今天?"
他看了看满脸惊讶的我们,又补充道:"别担心,这钱来路正当,是我这些年的积蓄,现在拿出来正好用在刀刃上。"
母亲接过信封,手有些发抖,眼中泛起泪光:"弟啊,你有心了,可是这么多钱,你从哪来的?听说你工作不太顺利"
这时,院子里飘来邻居家做饭的香味,混合着傍晚的微风,让人心里升起一种温暖的感觉。
小舅叹了口气,道出了实情。
原来他大学毕业后,没能如愿进入国家机关,在一家外企做了两年,又被裁员。
之后他尝试做过贸易,开过小商店,几次创业也都失败了。
正当他一筹莫展时,偶然发现县城里的学生缺乏安静的学习场所,于是他凭借着大学里学到的知识,在县城最繁华的地段租了一间门面,办起了一家自习室,专门为备考的学生提供安静的学习环境。
这个小生意虽不起眼,却在教育升温的年代里渐渐有了起色。
后来,他又添置了一些图书和复习资料,提供给学生们借阅,自习室的名气越来越大,甚至吸引了周边乡镇的学生。
"最重要的是,"小舅眼中闪着光,"我在自习室里设立了一个特殊的奖学金,叫'姐姐的嫁妆',专门资助那些像我当年一样贫困但有志气的孩子。"
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照片,上面是一群笑容灿烂的年轻人,背景是各个大学的校门。
"这些年,已经有十几个孩子在我的帮助下考上了大学,有的已经毕业,在各行各业做出了成绩。"
听到这里,我不禁热泪盈眶。
一直以来,我只知道母亲帮助了小舅,却不知道她的这份恩情已经传递给了那么多陌生人,像一盏明灯,照亮了更多人的前路。
"当年姐把嫁妆变卖给我上学,其实是放弃了自己进城工作的机会,"小舅看着母亲说,神情严肃,"那时候姐姐本来可以通过纺织厂的关系,调到省城去的,条件是自己负担路费和安置费。"
"可姐姐把所有钱都给了我,自己却留在了这个小县城,一待就是这么多年。"
我震惊地看着母亲,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
母亲的眼神有些躲闪,轻声说:"那都是过去的事了,不提也罢。"
"我发过誓,这份恩情,我要还三代。"小舅坚定地说,"从我到我的孩子,再到我的孙子辈,都要记得这份恩情。"
那个夜晚,我们聊到很晚。
小舅临走前,送给我一本笔记本,扉页上写着:"知识改变命运,善良传承希望。"
那本笔记本陪伴我度过了大学四年,每当我遇到困难想要放弃时,就会翻开它,想起母亲和小舅的故事,重新找回前进的动力。
大学毕业后,我本可以留在大城市,却选择回到家乡,利用所学专业知识,创办了一个返乡青年扶贫项目,帮助更多的农村孩子接受教育。
我的办公室里,挂着一张老照片,是母亲年轻时穿着嫁衣的样子,脖子上戴着那条玉坠,笑得灿烂。
每次看到这张照片,我就想起她变卖嫁妆的那个春天,想起她眼中的坚定和她对知识的信仰。
有一天,一个面容黝黑的农村孩子来到我的办公室,怯生生地问能不能申请资助。
他的成绩很好,但家里条件困难,父母都是农民,供不起他上高中。
我看着他渴望的眼神,想起了当年的小舅,于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。
后来这个孩子果然没有辜负期望,不仅考上了重点大学,还获得了国家奖学金。
临走时,他送给我一个手工编织的钱包,说是母亲做的,希望我能收下。
"老师,"他声音有些哽咽,"我一定会像您帮助我一样,去帮助更多的人。"
看着他远去的背影,我突然明白了母亲当年的选择。
她或许并不知道小舅最终会有什么成就,但她坚信知识的力量,相信一个受过教育的人,能够创造更多的可能性。
如今,我的扶贫项目已经帮助了上百名学生,其中有不少已经成为各行各业的栋梁。
每当看到那些孩子们认真学习的样子,看到他们眼中闪烁的渴望和希望,我就想起当年母亲和小舅眼中的坚定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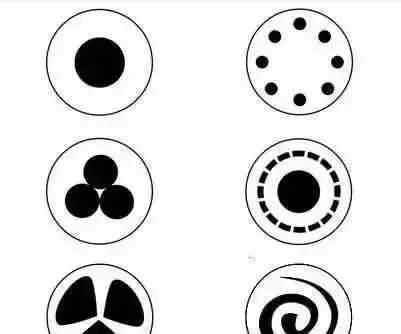
那份坚定穿越时空,跨越代际,成为照亮黑暗的光明。
母亲的嫁妆早已不知去向,但那份情谊却像一颗种子,在我们家族和更多人的心中生根发芽,见证着一个普通家庭教育观念的变迁与传承。
去年春节,全家聚在一起吃团圆饭,已经满头白发的母亲突然说:"当年变卖嫁妆的事,我一点都不后悔。"
她看着小舅和我,眼中满是欣慰:"看到你们现在的样子,我就知道,当初的选择是对的。"
父亲在一旁笑着说:"你啊,就是心软,不过这次我承认,你比我有先见之明。"
小舅举起酒杯,向母亲致敬:"姐,你的嫁妆没有丢,它变成了无数人生命中的光。"
我也端起杯子,心中满是感动和骄傲。
这或许就是最珍贵的嫁妆——不是金银财宝,而是一种精神,一种信念,薪火相传,生生不息。
它教会我们,人生最大的财富,不是口袋里的钱,而是心中的爱和对知识的渴望。
在这个普通的家庭里,一个普通女人的选择,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,也为我们树立了一座精神的丰碑。
每当夜深人静,我望着窗外的星空,总会想起母亲当年在当铺前的背影,瘦小却坚定,普通却伟大。
这就是我的母亲,一个用嫁妆点亮希望之灯的平凡女人。
她的故事,将永远铭刻在我的心中,激励着我,照亮着我前行的道路。

